- UID
- 116803
- 积分
- 0
- 精华
- 贡献
-
- 威望
-
- 活跃度
-
- D豆
-
- 在线时间
- 小时
- 注册时间
- 2004-3-24
- 最后登录
- 1970-1-1
|
马上注册,结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让你轻松玩转社区。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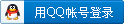

×
西岭雪
我第一次注意到她只是因为她知道《吉赛尔》,这使我多少有些意外她是卡蒂亚的女朋友,叫“诗柔”是中文的“雪”译成英文“SNOW”再音译回中文,麻烦得很,不知道为什么现代白领会对这个游戏乐此不疲。想想好笑,半通不通的英文大举进攻国内所谓白领阶层时,人人以一个英文名字为荣。就像卡蒂亚,直接以钻石品牌为名。但是各种PETER、ROSE多了以后,雅痞们又觉得这也显得老土,用回中文名吧,又不大甘心,以为倒退,于是再绕一回弯儿,把英文再译成中文。
这也难怪,时尚本来就是以繁琐为标志的。喝咖啡都要做成冰淇淋模样,又怎么能怪都市名媛人人一身“三宅一生“?不过诗柔倒没有穿“三宅一生“,也不喝”卡不奇诺“,而是老老实实要了一杯”哥伦比亚“自磨。她的手势很老练,看得出来是常自己做咖啡喝的。而且 她知道吉赛尔,这说什么都比卡蒂亚那些只知道阿兰德龙的女伴要高明许多。记得有一次我在卡蒂亚的朋友面前无意中谈及帕瓦罗蒂,居然有个女孩问我那是不是一种新的服装品牌。从那以后我就发誓绝不再轻易说明身份。
但是今夜有些兴奋,是因为红酒吧?或者是诗柔那一身堪与红酒媲美的水红绸裙。破天荒的,我同她交换了名片,上面印着“音乐家何甘声”,这就是我。哈,我是个音乐家。唱歌剧的。在以前的中国,这叫戏子,但是现在,时代不同了,我是音乐家,而且是留过洋镀过金的有独立经理人的音乐家。即使在美国我也是属于上流社会的。但是我却并不自由,我的生活被每个月接踵而来的合同和续约完全地占,我的衣食住行都得听经理人的安排。总是笑得见牙不见眼的经理人似乎比我更惬意更成功。很多的时候我都搞不懂,我是在为经理人服务还是经理人在为我服务。这次说破了嘴,才争取到一年的假期,可得好好消受一番。
沉思默想中蓦然抬头,只见诗柔很大方地笑着,微微歪着头,一头长发披泻下来,不说话也像在挑逗:“你也唱罗密欧?”我不由的醉了。我甚至站起身,执红酒杯,放声高歌。唱的是意大利咏叹调,我不相信那些叽叽喳喳的女孩子们会听得懂,但是她们全体静下来,艳慕地看着我。唱的是熟练的意语,而且我来自美国,这就够了。如果我愿意,我想,或许不必开后也可以俘虏这些女孩子的心,只要给她们看一看绿卡足矣。
卡蒂亚说过每个来自国外的成功者在国内至少拥有一个以上的女朋友。我不知道我算不算成功,但是我只有卡蒂亚一个。尽管我们不是很合得来,但是她是我的未婚妻。我这次回国,这是为了筹备婚礼。他不是特别漂亮,但高挑,丰满,有很长的睫毛和很黑的眼珠,而且家教严格。我在国内的时候,我们同居;我不在,她则住在父母家。我父母和她父母是三十年老交情。这些理由,已经足够让我娶她。尽管,她也不知道帕瓦罗蒂。她甚至不知道掉红轩,以为那是一间咖啡屋。是什么时候,祖国的女孩子变得这样的浅薄无味?那些抚古琴读太上的葬花人哪里去了?
在国外日日思乡,可是回来以后,才觉得故乡早已不是梦中的故乡。这里没有张爱玲的月亮,没有鲁迅的戏社,没有老舍的茶馆,甚至没有琼瑶剪剪风。这里什么都没有,只除了对美国一味的模仿与赞叹。这里,甚至比美国更像美国。我觉得失落,我是回来寻根的。可是回来了,却怀念起美国了。到底哪里才是故乡?或者,哪里才是异乡。
我,是一个没有根的人。
我对着卡蒂亚和诗柔微笑,醉态可掬:“告诉我你们的名字……不不不,是中文名字。你们的父母难道不是中国人吗?没有给你们取一个中国名吗?”我指着所有的女孩子嘲笑“女孩子最可贵的品德不是矜持吗?为什么你们争着暴露?告诉我,这里面还有处女吗?有一个处女吗?”
女孩们站起来,大概她们以为我在耍宝。卡蒂亚扶住我:“你喝醉了。”
我倚在卡蒂亚身上,眼睛却望着诗柔:“如果我说我没醉,你们一定会说喝醉的人才说没醉;如果我说我醉了,我等于成认了你们的话。你们是不是这样子设圈套的?现在的女孩子的机智是不是都用在这些对白上了?”诗柔忽然站起来,迎视着我,静静的说:“我不懂歌剧,但是我会背《春江花月夜》,而且,而且,如果你会弹《高山》,那么我或许会和一曲《流水》。”
我不禁大笑起来,觉得这场PARTY真是有趣极了。
卡蒂亚的眼睛却忽然冷了,她说:“我不该让你陪我来。”
她说她不该让我来,为什么?是为了诗柔吗?可是明明是她强拉我来的。
这,就叫做作茧自缚吧?我又笑了。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头一侧很痛,仿佛有锤子在一下下地敲击。
卡蒂亚递给我一条热毛巾,问:“要咖啡还是要红花?”
她关切地望着我,眼珠漆黑,长睫毛微微颤动,仿佛她的灵魂在舞蹈。可是她却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女子。她所有的,不过是“第五大街”的香水和“花花公主”杂志。不过她看的是英文版,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学问。不知为什么,经过昨夜,我对卡蒂亚忽然之间多了许多挑剔,是因为诗柔吗?诗柔有灵魂吗?
卡蒂亚说:“你昨晚喝得很醉,好在没有吐。不过也不是好事,留在肝经上,会更伤身。
”
她对我是真的关心。我有些感动,抱住她的腰撒赖:“我的头痛得很,帮我揉一揉好不好
?”
躺在卡蒂亚大腿上享受按摩的时候,我在想,不知诗柔有没有男朋友,会不会也这样地为男朋友按摩。在一个女人的怀中想着另一个女人,我觉得自己有些可耻。可是,我不能自己,希望见到诗柔,与她合奏一曲《高山流水》。但是这个机会一直没有等到,卡蒂亚不再带我到她的女伴们面前炫耀,偶尔聚会,诗柔也总是缺席。我有些怀疑卡蒂亚存心,但也不好开口去问,只是在那些胭脂派对中比以往更
加沉默。
这样子一直到了圣诞节,本以为这是西方的节日,与中国没什么关系。可是不然,如今的新派女郎是宁可不过春节也要过圣诞的,而且好么像模像样地举办酒会。大厅正中的圣诞树金壁辉煌,而女郎们浓妆艳抹也正如一棵棵会走路的圣诞树。不知是酒还是香水,我又有些醺然,只知对每一个经过身边的女郎微笑,口才却是笨拙的。这时,一个穿黑丝绒晚礼服的女郎站到我的面前,轻轻的说:“又见面了。”
我的舌头立刻灵活起来,“这真是最好的圣诞礼物。”
这是诗柔。见到她我才意识到,我一直在等她。
我看着她,清澄的眼睛,秀挺的鼻子,除淡淡唇膏外,看不出化妆的痕迹。不过我当然知道她并不是没有化妆,而是在化妆时比一般女人用了更多的心。所谓淡极始知花更艳,这个道理我晓得。
她笑着,露出细碎而整齐的牙齿,这使她显得小巧。她说:“我们今晚会有好节目。”
“是什么?”
“焰火。”
“焰火?”
“是。我们藏起了许多烟花炮竹,你知道广州是不允许放鞭炮的,不过没关系,晚上我们会去城郊河滩上放,放完立刻开车跑,保准不让警察抓到。”
我动着脑筋:“如果,我们不仅躲过警察,也躲过所有人,你说是不是更好玩?”
“你是说……”
“我们现在就走,悄悄把烟花放了。等他们和警察一起发现漫天烟花的时,我们已经跑掉
了。”
她纵声笑起来,忽然间变成了一个淘气而任性的顽童。
所有人的目光被她一起吸引过来,卡蒂亚立刻走近,说:“诗柔,我还以为今晚你不来了
。”
所以她才会带我来,我知道。诗柔仍控制不住地狡黠地笑着:“我胃痛,本来以为来不了,可是后来不疼了,就来了。”她边说边走,话说完,人已经走开好远,可是远远地向我送了一个眼风。我会意,微笑不语。卡蒂亚问:“刚才你们在说什么,那么好笑?”
“在说谜语,等下告诉你谜底。”谜面由我一手制造,说实在话我也很想纵声大笑。
我托辞上洗手间避开卡蒂亚,然后迅速从后门溜出,诗柔已经在车上等我。
她有一辆私家“神龙.富康”,她告诉我,后车箱里有满满一箱烟花炮竹,可以炸毁整个兵工厂。这使我的热情空前高涨,觉得我们不是去玩,而是去执行一项非常恐怖危险的重大特务行动。
我太紧张,不得不说些闲话放松一下,于是问诗柔:“怎么圣诞节不同男朋友在一起?”
“我没有男朋友。”
“鬼话。”
“真的。男人们不喜欢我。”
“为什么?他们都是瞎子?”
她微笑,表示接受我的恭维,停一下又说:“他们不是瞎,恰恰相反,是太明白。他们知道娶老婆是娶老婆,找情人是找情人,但是我是那种总是把老婆与情人混为一谈的人。”
“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做了人家老婆,却要人对我像情人一样;做了人家情人,又非要人娶我做老婆。”
我明白了,她的话听起来玄,说穿了却很简单,就是向婚姻要爱情。可是,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对。
我这样子对她说了,她忽然眼泪汪汪起来。过了很久,叹了口气,却什么也没有说。
她没说,但我也明白她的意思。我不知自己的心是喜是忧,我终于知道,她对我同我对她是一样的,可是我也知道,我已经有了卡蒂亚。
我们把车子一直开到城郊,然后在一片荒滩上放弃烟花来。哦,烟花真是美丽,一朵一朵,瞬间绽放,灿烂纵性,转瞬即逝,有如青春。诗柔把所有的烟花堆在一处,然后将披肩点燃抛到烟花上,拉着我飞奔至停车处,发动引擎。身后是惊天动地的爆炸声,然后大蓬的烟花冲天而起,灿烂不可言喻。我为之神眩目驰,振荡得说不出话来。诗柔一路狂奔,只是不时自倒后镜里观看烟花绽放的胜景,然后一下开到她认为安全的地方才停下来。
我们下了车,远处烟花已稀,但仍有哑哑的爆竹声时时炸响。诗柔笑着,她的裸肩在星光下异常的美丽,泛着珍珠般的光华。我脱下西装为她披上,却不放开抓着西装的手,将西装连她一同拉近,裹进我的怀中。
我们在烟花灿烂间拥吻,我的心亦如烟花般开放。这一刻,我知道她就是我要找的女人。
不论我们会不会和谐地共奏一曲《高山流水》,但我们一定是彼此寻找的那个音符。
我饥渴地在她的口中吸吮爱的甘露,连同眼泪。
她说:“我最恨做人家情妇,却还是做了。“
等一下,又说:“你要了我,我就是淫妇;你不要我,我便是弃妇。总之有罪。“
我知道她是指卡蒂亚,我安慰她:“交给我,不要再想。”
我决定第二天一早便去同卡蒂亚摊牌。
可是卡蒂亚根本不等我准备好,聪明的她直接等在诗柔宿舍门后,一副捉奸捉双的架式。
她铁青着一张脸,身上仍穿着礼服。妆已经残了,比不化还惨。存心要扮演怨妇,故而一声不吭地看着我们,满眼哀愤。
我和诗柔愣在门前,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而我的一只手臂还环在诗柔肩上。
诗柔最先开口,她取出钥匙,淡淡的说:“你们是进来谈,还是会回去谈?”
卡蒂亚忽然哭起来,她看也不看诗柔,只望着我:“你是不是很得意,有两个女人这样子为你争风吃醋。”
老实说我难堪至极,我不知道别的男人在这种情形下是不是会得意,我只知道自己不是那块料,我情愿她们两个都不理睬我,让我苦苦地去追。男人在这一点上是很贱的。
我低下头说:“卡蒂亚,我们不要打扰诗柔,我陪你回家。”
卡蒂亚这才回头望一眼诗柔,咬字很重地说:“那好,我们不打扰你,我们走了。”
诗柔扬一扬眉,想说什么,到底没有说,只是略微一笑,点点头,开门进去了。
真是潇洒得可以,扔下一个烂摊子让我收拾。
我对着卡蒂亚忏悔:“我对不起你,我无可辩解,我只有对不起你。”
“可是,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呢?”卡蒂亚追问。女人的心是坚强的,她们明明是痛,却仍要在伤口里摸索形状,哪怕让自己更痛也决不放弃。
我继续忏悔:“我第一次见到她吧,我说不清。我只有对不起你。”
接下来的日子,我每天对卡蒂亚说上数十遍对不起。在说第一千零一次时,她终于答应同我和平分手,而且永不相见。永不相见,她说的。
但是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谈恋爱或许是两个人的事,但结婚却是两个家庭的事。
我的父母和她的父母一起涌上门来逼我招供,于是我又对着全世界一遍遍的说:“对不起。”说了一遍又一遍,却得不到任何一个人的原谅。
我着实疲惫,反正是放春假,诗柔不需要上班,我干脆拉她陪我去乡下避难。
我们选择了梅州,因为听说那里的泮坑神庙非常有名。
说来可笑,两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人,巴巴地坐上飞机跑到大老远去,是为了到神庙磕一个头,求一个签。我们虞城地跪着,两个人四只手共摇一个筒,一下,两下,刚刚摇到第三下,一只签已“嗖”地跳了出来:33,下下。老和尚在一大沓黄纸条里撕下来一张,一大沓33签。我们的命,与许许多多摇第33签的人重合着,可是当事者永远以为世上万物只为了自己一个而设,自己是最与众不同的一个。
签文上说:“何等蹉跎复彷徨,临到头来费思量。劝君处身多忖度,世事一梦煮黄粱。”
老和尚解释:“就是说事情很复杂,施主应该多思量,看开点。世事沧桑,不过是过眼云烟,黄粱一梦。”说了等于没说。
诗柔却信服地不住点头,又问:“我们的确应该多想想,可是到底该怎么做呢?”
“三思而后行,事后都是空。看开点,要保持心境平和。”
“老师父,我这求的是姻缘,依你看,到底能成不能成呢?”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有缘人终成眷属,一切都要看个缘字。”
“那我们到底有缘没缘呢?”
“缘字一字,十分难解。相遇是缘分,相识是缘分,你们今天到我这里来也是缘分……”
我再也忍不住,拉起诗柔便走。什么江湖术士,背熟了两句似通不通的俗话,就冒充得道高僧。像他那样子信口胡说,讲一句是一句,讲一百句也是一句,我也可以挂牌开张,还说得比他清楚流利呢。至少普通话比他来得标准。不过也难说,也许他其实会说普通话,就是故意讲客家方言,让客人更加似懂非懂制造神秘感的。
诗柔却总是闷闷不能释怀,犹豫说:“满筒里那么多签,偏偏掉出这一枝。又那么早地跳出来,总是有点道理的吧?”
我取笑她:“亏你还是北大毕业的高才生呢。迷信起来也和村妇差不多。筒子里不是上就是下,摇出来哪一枝都有道理还了得?你听老和尚不是说了吗?世事沧桑,黄粱一梦,所以我们更得珍惜时间,珍惜现在,好好开心才是正经。”
诗柔很温顺,当真不再提不开心的事,只随了我胡天胡地四处潇洒。我们去百花洲购物,去桥头镇吃狗肉褒,盖浇饭,去邮电花园地老华桥石像下合影,去公园划船,手牵了手从夜里一直散步到黎明,忽然听到几声鸡叫,发现原来已经不知不觉到了郊外。
梅州石那么小,我们的欢乐却那么大,大得整个世界都装不下。我对诗柔说:“我一定会娶你,全世界也不能阻止我。我不是为了你,是我自私,为了我自己,因为没有你我不知道再怎么活下去,我再也不会快乐。“
诗柔对我说:“世上有许多人结婚是为了经济,为了家庭,或者干脆是为了已经到了那个年龄,但是如果我们结婚,却一定是为了爱情,于是我们会是婚姻中最幸福完美地。”我们整夜地说着这些甜蜜的傻话,一点也不觉得肉麻,两个骄傲的物质的自命不凡甚至有点玩世不恭的人,掉进爱情陷阱之后竟也同一般十八九岁初恋男女一样甜蜜而痴傻。
以至多年之后,当我想起梅州的那一段,总是怀疑记忆的真实性。因为在那以前和自那以后,我都再没有过那样的疯狂与单纯。
疯狂的爱情,单纯的快乐。我常常遗憾。如果在那个时候我或者诗柔任何一方出了一点意外,我们的爱情也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凄美但最完整的经典故事。但是我们石这样地平凡,平凡得生命中连意外也不来光顾。
一个星期后,我们安全地回到了广州,重新面对七姑八婆的数落指责。我烦得想要自杀,
私下里同诗柔商量:“算了,不如我们私奔也罢。”
诗柔苦笑:“如果是私奔去美国,我不反对,至少你有正当职业与高尚身份,我们的温饱
不成问题。但是在国内,我们可以去什么地方?到梅州去唱意大利咏叹调?唱给谁听?”
歌剧在中国没市场,这是事实。而且,最关键的,我没有“组织”。
说来好笑,我在自己的祖国,当自己是客人时会得到一片掌声与热情欢迎,被敬为上宾,持绿卡的人上之人;但一旦真想回来做主人,却发现不过是个下人,沿街乞讨尚不知路人肯不肯买歌剧的帐。我的身份,就像我的歌剧一样尴尬,进得了大雅之堂就成为了阳春白雪,如果不能,则连下里巴人也不算。我必须回去——“回”——到——“异”——乡!
可是我的护照被扣在母亲那里,我不得不乡卡蒂亚求情,让她代做说客,让我父母放我出笼。
说来惭愧,让前头人替自己为了现任女友的事情说情,是很残忍的。可是我没有别的办法好想。但卡蒂亚是个大度的人,这时候是表现她大家闺秀风范的良机,她不会放弃这样好的表演机会,于是打扮得仪态万方地向我母亲请安来了。欲语先笑,话里有无限未尽之意,含蓄蕴藉,委曲求全,刚刚寒暄几句已尽得老人家怜惜。
母亲大人含了泪安慰:“好孩子,你这么千里挑一的一个人,怎么他就辜负了你呢?”
卡蒂亚低头叹息:“阿姨别说这样的话,他总是有他的理由。”
我在一旁瞠目,彷佛看戏,《红楼梦》里薛宝钗承欢老太太的一出。
那诗柔不成了林妹妹?但是转念间我又不由对自己嘲骂,你又算哪门子的贾宝玉?
当下只听“薛宝钗”深明大义地又说:“他并不是这世上第一个变心的人,他毕竟没有骗我,他也不是坏人,我想他心里也不好受。”
字字都是金玉良言,只是这样当面骡对面鼓地说给我听,到底有些吃不消,我咳嗽一声,正想把重复了一千零一次的对不起再说上第一千零二次,“贾母”大人却在一旁发话了:“我不管现代人是怎么样地朝三暮四,咱家里总之没有这样狼心狗肺的人。
他不悔改,我怎么也不答应的,要么他给我一个婚礼,让我看着他风风光光地娶你过门;要么我给他一个葬礼,让这个不肖子给我披麻戴孝,让天下人戳他脊梁骨说他气死老娘。
“听听,听听,这是哪朝哪代的对白!可是别说,仍然有它的威力所在,我不得不低了头上前求饶:“妈,你这说的是什么话?我和卡蒂亚的事,让我们自己来解决好不好?卡蒂亚是明白我的。”一边说一边向卡蒂亚递眼色。卡蒂亚狠狠瞪我一眼,摇了摇“贾母”胳膊说:“阿姨,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想替我出气,可是您想一想,这样子闹过一次,我们怎么还能在一起吗?就算他现在立时三刻回心转意来求我啊,我也不会从前那样待他了呢。强扭的瓜不甜,这道理我懂,您还能不知道吗
?他是个孝子,可我也是个烈女啊,他遵了您的意娶我,我为了我自己,我还不嫁呢。”
这一番话说得老妈目瞪口呆,她大概没从这个角度想问题。我不由得乐了,原来孩子是自家的好,她嘴上骂得恨,心里却当我是天字第一号宝贝,人人争着抢着要的。
老妈愣了半晌,忽然露出一脸倦态来,挥挥手说:“你们的事,我也闹不懂,由得你们自己去办好了”
事情竟解决得这样顺利,我只差没跪下来大呼皇恩浩荡。
走出门来,我头如捣蒜地对着卡蒂亚连连道谢,自觉是天下第一罪人。卡蒂亚却仍是言笑晏晏:“算了,只要你仍然当我是朋友,就算是谢我了。”
我惊喜:“我只怕你再也不愿见我。”
永不再见,她亲口说的,这句话原是横在我心口的一块大石。现在她自己把它搬开了,我有一种守得云开见月明的轻松。
当晚我请卡蒂亚去“白天鹅”喝咖啡,庆祝彼此尽释前嫌。卡蒂亚带着一个沧桑的笑对我说:“现在我是你的红颜知己了。”
这场婚变令她成熟深沉了许多,长睫毛下一双深不见底的大眼睛越发漆黑越发灵动,如今,那里大概真地有一个灵魂入住了。
接着我和诗柔的婚礼兵荒马乱的操办起来。
不不不,这并不是说大家对我们有多重视,而是因为我已经拿了绿卡,在办证件上凭空多了许多跨国烦恼。每一份文件每一次盖章都费尽周折,三四个月下来,人也累得瘦掉一圈。例行公事地隔一天见一次诗柔,除了汇报办证进展再没有一句别的话。所有的事都得拿出来有商有量,但不过一两句便算言尽,常常吃顿饭也不说一句话。那样子,看上去很想一对夫妻,但太像夫妻了,已经没有一丝一毫浪漫。还没结婚倒已经携手半辈子似的。
相反是卡蒂亚,很难得才见一次面,倒是有说不完的话。相识几年,彼此有太多共同的回忆,问一问近况,也都是决不虚伪的关心。
一日约她午餐,听到隔壁一位妙龄女郎清清楚楚地在抱怨:“我们每晚通电话至深夜。”
“聊什么?”
“还有什么?他老是抱怨公司运转不灵,全身上下没一点浪漫细胞。”
我与卡蒂亚相视而笑,男友是商界忙人仍不忘每晚致女友亲密电话,还要被抱怨不解风情。这女郎活脱脱为“身在福中不知福”这句老话的现身说法。
卡蒂亚笑道:“这年头男人也真不易做。”
我应她:“所以你真是天下男人的红颜知己。”
卡蒂亚叹息:“男人们总是娶对自己不过尔尔的女人做妻子,赴汤蹈火地对她好;却对那些曾为了他们赴汤蹈火地女人不过尔尔,最多颁一个红颜知己的安慰奖。”
我苦笑。卡蒂亚又说:“或者说,男人们总是赋予需要他们帮助的女人以无比的爱心与耐性,却仇恨帮助过他们的女人。”
我如坐针毡:“卡蒂亚,你是不是最近要出一本《男女真经》?”
卡蒂亚正容:“是我过分了,甘声,别生我气。”
“是你别生我气才真。”我再次道歉,“卡蒂亚,过去的确是我……”
但她不让我说完:“甘声,你没什么不对。人们当然懂得选择什么最合适自己。是我太小气,我以后不会了。只是,”她低下头,幽幽轻叹,“我只是忘不掉。”
哦,我只是忘不掉,那样轻轻的六个字,被她说得缠绵婉转,荡气回肠。我只觉一阵鼻酸。当天夜里,我一次次回想着卡蒂亚的神情语言,放弃她原是觉得她不够浪漫,不够刺激,不够有性格。可是现在看来这一切全属误察,是我自己不懂欣赏。我第一次开始怀疑,我的选择是否错了。
但到这时候已经不能回头,不然前面那一大圈周折更加无谓无聊,都不知是为了什么。
于是我惟有继续挣扎忙碌,可是诗柔并不领情,她不住指责我:“你现在同我在一起已经不再快乐,那么又何必为娶我而奔劳?你是不是后悔了?你觉得我其实并没有你想象中好,为了我而放弃卡蒂亚并不值得?”
我看着她,内心只觉得疲惫不堪。无论她也好卡蒂亚也好,其实都是城市中的佼佼者,娶到谁都应该是我何甘声毕生至大成就。可是我发现我却谁也承载不了。
最重的负担是婚姻,男女之间永远是停留在恋爱拿一个阶段最为美好,一旦谈婚论嫁便显得生分。我怀念初认识时的诗柔,慧洁,灵性,充满感觉;我也留恋现在的卡蒂亚,大方,深沉,风情万种,悲哀的是我只能选择其中之一,更悲哀的是我必须选择其中之一。再挑剔,我也不过是女人们的战利品而已。
我拥抱着诗柔说:“我是一定会娶你的,别再给我压力,别逼我强颜欢笑。”
诗柔更怒:“是我逼你娶我吗?你又何必强颜欢笑?我知道你内心有抱怨,如果爱不再令你轻松,我们不如分手。”
分手?说得轻巧。我在这个时候提出分手,简直只剩下自裁于天下的惟一出路了。
正如我自己说的,这个时候我惟有强颜欢笑了:“你说哪里话?你知道我是爱你的。我只不过为了签证的事烦恼。”
我开始怕见诗柔,频频躲进卡蒂亚的温柔乡买醉。卡蒂亚嘲笑我:“你为了娶我而回国,现在倒娶了别人。原来还以为你够狠,也罢了,总算有三分硬气。现在看看,其实还是拿不起又放不下。你再这么着,我拿笤帚扫你出门。”
我厚着脸笑:“你才不舍得,你是我的红颜知己。”
卡蒂亚红了眼圈:“被你冠一句红颜知己,我下半辈子也就不用做人了。我们已经不再是未婚夫妻,你还这么三天两头地上门,别人不说闲话,我自己也看不下去。”
我被卡蒂亚说得低下头去,自觉是天下第一自私之人,太没担待,不太替人思量。可是内心又忍不住替自己辨白,我若果然没承担,若不是替别人着想,现在也不必结这劳什子婚了,拍拍屁股回美国才是正经,可以继续我黄金王老五的快活风流。
那个晚上,我又一次在卡蒂亚家中大醉。大概在夜里十点多钟,我被推醒,坐在我面前的,是诗柔。她很平静的说:“卡蒂亚通知我来接你。”
我一惊,酒醒了大半。卡蒂亚根本不屑于乘人之危,却趁这个机会向诗柔做了一次漂亮的反击。自己的未婚夫在前任女友家烂醉如泥,而人家却大度地完璧归赵,这次诗柔一定觉得颜面大失。但她的脸上却看不到任何表情,只是礼貌地向卡蒂亚道谢,体贴地为我递了一块热毛巾。
我羞愧,内心惴惴不安,不知该如何解释。不料诗柔并不问起,将我送到家门口,也不下车,便若无其事地摆摆手走了。
我更加不安,惟有化惭愧为忙碌,更加起劲地为签证的事奔走。
到了6月,事情已经准备得七七八八,只差结婚证和诗柔的签证没有最终批下来,但已是累得人仰马翻,连喝庆功酒的力气也没有。老妈开始翻黄历算日子,我向诗柔建议婚礼仪式简单点,然后去美国补度蜜月。诗柔不允:“整个圈子里都知道你原来是卡蒂亚的未婚夫,我是半路杀进的程咬金。恶名儿已经担了,再不风光操办,还以为你是被迫结婚,所以不愿见人呢。”
我瞪着她,没想到那样出尘脱俗的一个人,竟然也有这样市井的想法。但是我自从那日醉酒,心里有愧,已经习惯不同她争吵,于是全盘答应下来。
妈妈起初是不满意诗柔的,但既然木已成舟,注定以后叫妈的只能是诗柔,她便也只有接受下来。才有一点眉开眼笑,诗柔已经打蛇随棍上,一天12小时在母亲处当更,找酒店订酒席一概尊老妈为首席顾问。老太太自觉情分矜贵对这个准儿媳妇日渐接纳,看到卡蒂亚时再不如以前亲热,客套疏淡了许多。还没行礼,诗柔已经一口一个妈叫得亲热火辣,清清楚楚地叫客人觉得内外有别,让我越发觉得此人其实不可小觑,这才知道原来这世上早已经绝迹了林黛玉,个个美娇娘都是城府深沉的薛宝钗。
也许我应该庆幸,婆媳和睦毕竟是一件好事,可是内心不知怎么地,却只是感到失落。
婚礼定在7月8日,可是到了6月底结婚证还是没有办妥,双亲大人当机立断:“改日子是不吉利的,婚礼照办,有没有证都办,反正早晚的事。”
7月3日晚我和诗柔一起推敲酒席程序,又研究到底是请张律师做司仪还是到礼仪公司请一位专职人员。正罗嗦着,诗柔看一眼表,说:“呀,快三点了,我忘记开电视,欧洲杯决赛。”
我一愣:“我倒不知道你还是球迷。”
诗柔一笑:“你不知道我的事多着呢。今晚是法国对意大利,我们来赌一赌吧,你猜猜谁会赢?”
我看一眼屏幕,现在的比分是1:0,意大利领先一球。
“当然是意大利队,已经下半场了,法国队扳平的机会不大。”
“那不一定。”诗柔仿佛存心抬杠,“我同你赌,法国队一定会后来居上。”
90分钟比赛已经结束,进入伤停补时阶段,而意大利队仍以1:0稳居前座,我宣布:“最后一分钟了,除非奇迹出现,意大利队已经是冠军了,我仿佛已经看到他们举着奖杯绕场一周。”
话音未落,忽见法国队大军压境,前锋13号在禁区边缘大脚抽射,意队门神托尔多就地扑倒,已经扑到球了,却只是轻轻以沾,足球着了魔似的溜溜转,打他腕下一擦而过,施施然进了球门!
满场雷动,托尔多倒在地上抱头痛呼,我睁大了眼睛不可置信,诗柔却一跃而起,大声欢呼起来。
老爸老妈都被惊动了,走出来问发生了什么事,诗柔眉飞色舞,连说带比:“上帝是法国籍的,在最后一分钟,不,是最后12秒钟,法国队毫无道理地射进了一个球,现在是一比一平,如果加时赛里仍不能分出胜负,就又要来一场点球大战了!意大利队是凭点球大战赢了荷兰队的,一直如有神助,可是今天好像已经被神抛弃,他们的运气结束了!”
她兴奋得这样夸张,让我觉得她不是在说足球,而是在说她自己。她便是法国队,而卡蒂亚便是意大利队,本来已经是领先一分的,可是临时婚变,如今被诗柔后来居上,连老妈也不再支持卡蒂亚,而是一边倒地倾向了诗柔。就好像现在,她明明是被打扰了睡眠,却丝毫不以为忤,反而很高兴诗柔跟她有说有笑似的,很热心地说:“是吗?这么精彩!我也看看,到底哪一个队胜者为王。”
老妈也来看足球,而且是凌晨四点,这比法国队在最后12秒钟进球还让人惊讶。我忽然有一种感觉,上帝是站在诗柔这一边的,大概法国队真的会赢!
那么如果说诗柔是法国队,卡蒂亚是意大利,那我呢?我该是什么呢?教练?领队?或者是足联盟?
正胡思乱想着,只听见诗柔“噢”地一声又跳了起来,又叫又笑,不亦乐乎,我定睛再看,只见托尔多再次倒在了绿茵之上,一副不打算继续为人的放弃,却是法国队金球得分,已然赢了。
我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郁闷和失落,不是因为赌输给诗柔,而是觉得世事变幻,有如球赛,太不可测。
诗柔得意地问我:“如何?我说法国队会后来居上吧?”
我闷闷地答:“赢得毫无道理,全凭运气,胜之不武。”
诗柔不以为然:“赢了就是赢了,这是事实,要什么道理?”
电视上,法国队的队员们拥抱在一起,又唱又跳,又举奖杯,摆出各种姿式拍照,完全不觉得这场赢球有什么不妥。赢了,就可以夺冠,就可以得奖,就可以睥睨天下,傲视同侪,就可以扬眉吐气,要多么张扬就有多么张扬。谁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分明从来都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赢了就是赢了,怎么嚣张都是理直气壮地在享受成功。输了的人只有在一旁陪衬,风度再好也没有用,输了就是输了,什么也得不到。
我仿佛有些懂得诗柔了。
7月8日,婚礼如期举行,请了整整24席客人,隆重烦杂。诗柔前后换了五套礼服,打扮得天仙下凡一般,每次出场都爆起一片掌声。
卡蒂亚没有来观礼,只托人送了礼品,是一对金表。出手之阔绰令我心中越发黯然,她的气度的确没话说,但不论多么大度,她终究还是回避了婚礼,没办法当面锣对面鼓地面对自己的失败,把风光完全让给了诗柔。我站在诗柔身旁,满心里只有卡蒂亚,我不知她此刻是否在流泪,更不知她的心可会流血。
我只知道,我的心代她而疼痛,一阵又一阵,仿佛又线牵扯,那,就叫情丝吧?
散席时,诗柔走近我说:“你好像并不开心。”
“谁说的?我当然开心,我只不过是有点累了。”
诗柔微微一笑,眼底忽然掠过一抹沧桑。
但是婚总是结过了。我有一种尘埃落定的慵懒,这才知道其实有没有灵魂并不重要,因为实实在在的,从此我们的肉体已属于对方。我们会白头偕老,相敬如宾。我们会有两子一女或者更多,既然我有这个能力抚养,就不介意有很多个孩子,然后为他们洗尿布,热奶瓶,报学校,盖房子,鞠躬尽瘁,于是一生便就忙忙碌碌地过去,空虚也充实,不再有时间去追究灵魂与思想的问题。
我的孩子会在美国出生,他们不会再为故乡和异乡而困惑,而苦恼,而迷失,他们于美国就像我之于歌剧,如鱼得水,相得益彰。
在我结婚的那一天,我已经把我一辈子的书写完了。
我是在夜的醉梦里过完了我的一生。“劝君处身多忖度,世事一梦煮黄粱。”不,不必再忖度什么了,已经既成事实,生米煮了熟饭,这碗黄粱是只有咽下去了,哪怕味同嚼蜡,也只有与君共勉。
醒来时只觉今昔何昔,浑身无力。我摸一摸身边,是空的,诗柔已经起来了,但是枕边竟有一张纸,我拿起来,揉一揉眼睛,不过是潦草的几行,眨眨眼就看完了,却一时闹不懂是什么意思——
甘声:
你好!
我走了,不必再找我。我们的故事已经写完,有始有终,有高潮也有结局,很完整。我已经很满意。不知怎么的,我们的爱情变成了一场战争,而我要求自己,一定要赢一次。所以,我非要得到这次婚礼不可。谢谢你给了我一个隆重的婚礼,一次庄严的颁奖,清楚地让我知道,即使你不打算爱我一辈子,却已经决定照顾我一辈子。
但是你说过,我是一个向婚姻要爱情的人,然而我们的婚姻还没有开始,爱情却已经结束了。再留在你身边已经没有意义。好在我们并没有领取结婚证,而我也不打算再留在广州,至于我去了哪个城市,不要问,因为暂时我自己也不能确定。
保重!
吉赛尔
她的落款是吉赛尔,那个因为失去了爱情伤心猝死的牧羊女。她说她的爱情已经死了,她要开始新的生命。吉赛尔没有恨过王子,在重逢时她曾奋力保护于她。诗柔也并不恨我,如果有缘重逢,大概她也会成为我另一个红眼知己。
我的未婚妻,在同我分手后仍能彼此关心,究竟是一件幸事亦或不幸?
我伏在床头久久不能还魂。原来,我并不是她与卡蒂亚的领队或者教练,我不过是一个多余的裁判,在比赛中似乎地位显要,引人注目,但比赛一旦结束,无论谁赢谁输,都不再与我相关,谁见过球员们拥抱裁判一同庆祝的?诗柔骄傲地赢了,卡蒂亚大度地输了,而我这个裁判则在比赛后被弃置一旁,再没有谁愿意看我一眼。
也许我应该理解诗柔,其实她从头至尾都没有改变过,改变的只是她与我的距离。
有些人结婚是为了年龄,有些人结婚是为了经济,有些人结婚是为了责任。都还好过一些。可是诗柔是为了爱情。于是便诸多挑剔,便愈发不甘,便罗嗦,便易碎。
我有什么理由怪她?我因为渴望爱情而放弃卡蒂亚追求诗柔,却因为不能再付出爱情而终于为诗柔所放弃。
原来人是不能为了爱情结婚的。就像夜不能以焰火照明。
我想起圣诞那日的烟花,开头灿灿烂烂轰轰烈烈,后来稀稀落落断断续续,再后来就无声无息灰飞烟灭了。
就像,我们的爱情。
我们,爱如烟花
*-*6 |
|
 如果你在论坛求助问题,并且已经从坛友或者管理的回复中解决了问题,请把帖子标题加上【已解决】;
如果你在论坛求助问题,并且已经从坛友或者管理的回复中解决了问题,请把帖子标题加上【已解决】; 如何回报帮助你解决问题的坛友,一个好办法就是给对方加【D豆】,加分不会扣除自己的积分,做一个热心并受欢迎的人!
如何回报帮助你解决问题的坛友,一个好办法就是给对方加【D豆】,加分不会扣除自己的积分,做一个热心并受欢迎的人!
 如果你在论坛求助问题,并且已经从坛友或者管理的回复中解决了问题,请把帖子标题加上【已解决】;
如果你在论坛求助问题,并且已经从坛友或者管理的回复中解决了问题,请把帖子标题加上【已解决】; 如何回报帮助你解决问题的坛友,一个好办法就是给对方加【D豆】,加分不会扣除自己的积分,做一个热心并受欢迎的人!
如何回报帮助你解决问题的坛友,一个好办法就是给对方加【D豆】,加分不会扣除自己的积分,做一个热心并受欢迎的人!
 如果你在论坛求助问题,并且已经从坛友或者管理的回复中解决了问题,请把帖子标题加上【已解决】;
如果你在论坛求助问题,并且已经从坛友或者管理的回复中解决了问题,请把帖子标题加上【已解决】; 如何回报帮助你解决问题的坛友,一个好办法就是给对方加【D豆】,加分不会扣除自己的积分,做一个热心并受欢迎的人!
如何回报帮助你解决问题的坛友,一个好办法就是给对方加【D豆】,加分不会扣除自己的积分,做一个热心并受欢迎的人!
 |申请友链|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辽公网安备|晓东CAD家园
( 辽ICP备15016793号 )
|申请友链|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辽公网安备|晓东CAD家园
( 辽ICP备15016793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