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ID
- 266895
- 积分
- 0
- 精华
- 贡献
-
- 威望
-
- 活跃度
-
- D豆
-
- 在线时间
- 小时
- 注册时间
- 2005-5-26
- 最后登录
- 1970-1-1
|
马上注册,结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让你轻松玩转社区。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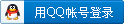

×
引言:迟到的现代性
1
20世纪之末,现代主义的实验室好像空无一人,它不再象能成为一个可以进行有意义实验的场所,也不再具有往常的先锋意义,以至于有人想把它放到博物馆中某个特定时期的展厅里,封存在一个历史的时间上,而不必身在其中。或许有人在问,1899年我们文化拥有的东西在1999年都失掉了什么?是热情、信仰、理想主义还是虔诚和探索的信念?实验室好象一座空空的营地,虽然它曾经收集了主人的美梦和梦想者的精神。如今人去室空,剩下来空荡的建筑令人生畏,其中只有一些痕迹般的元素如同符号被遗留下来,然而尘土再度耗蚀了它们,这里留存下来的,仅是用一种特定的执着等待再继续开始,以期待下一个试验的来临。
19世纪所有现代主义者━惠特曼、易卜生、马克思、克尔凯郭尔、波德莱尔都感受到了现代的不确定性,波德莱尔 [①] (Baudelaire)用他的诗歌描述了最早现代生活的画像,他创造了把城市作为现代历史之主体的观念;塞尚、蒙克用他们的绘画表现了时代的呐喊;同样,在20世纪末,人们也感受到速度的窒息,历史━以不同的方式在被重复着。如果说伟大的60年代,沉默的70年代,彷徨的80年代这样的说法成立的话,那么90年代,人们面对变化的无常变得更加犹豫不决,带着美好想往期待新时代开始的同时又对未来怀有一丝莫明的恐惧。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我们又想起上一个世纪末的人们所面临的同样困惑,这时,我们又能以怎样的方式回到过去史诗般的神话中,籍以解释这个被称为“多元主义”实际上却是混乱而平庸的年代。
2
后现代主义者和历史学家图谋把现代主义当作艺术运动,把它从科学技术、社会、 和经济条件演化过程关系中划分出来,而自身却以泛文化主义主流的身份从社会现代化中分离出来。这正是它昙花一现的原因。
正象于根•哈贝马斯 [②] (Jurgen Habermas)在他著名的演讲《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课题》中所指出的,“新保守主义者(指后现代主义者)切断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然后又为了某一方面的弊病(现代化)而遣责令一方面的实践(现代主义)。由于起因与结果的混淆,使之失去指责文化的‘对立’,尽管经济 的状况得到了肯定……事实上,一种新的肯定的文化已经被计划、被提出了”。尽管哈贝马斯批判现代主义的工具理性,但却是维护现代性的主要思想家。他对那些轻率和不负责任的批评启蒙时期人道主义理想和理性主义的人提出警告。(他的理论敌人主要是利奥塔等。)
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的文章《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③] 》是改变现代主义思考的重要催化剂,文中他解读了《浮士德》、《 宣言》等文本,他甚至倾向于19世纪的先驱们的观点。伯曼象拉斯金一样重新发现了早期现代主义传统的预言性,他希望重新唤起我们对早期现代主义的流行性、希望、集体意识和平衡的认识。他由于把保守主义者要放弃的现代主义从历史的垃圾里捡出来而受到批评,但他仍说道,我们应该尝试“把过去的现代主义中的一些能动的辩证因素带进今天的生活。”
肯尼斯•弗兰普顿(Kenneth Frampton) [④] 的学术框架建立在边缘理论的基础上,他的灵感更多来自发达世界的边缘,他相信“边缘的中心点会支撑建筑文化多层次的复杂性”。他在《地方形式与文化特性》一文中说道:“我们并不认为要创造一种史无前例的建筑形式,相反,我们知道,自己的任务是适度恢复一个设计运动(现代运动)所具有的创造性力量”。并且他认识到“重新恢复史诗时代的信仰体系和乐观精神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仍可以设想自己回归到建筑的现代途径上来”。在同一篇文章里,他把新历史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形容为“就是那些刚巧最不理智者,在通俗出版界眼中却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人们”,以及“建筑中通俗的历史主义,文化 中的新保守主义”。 他称自己的观点为“批判的地方主义”(Critical regionalism)。尽管他的文字具有隐蔽性,但还是能体会出他对现代主义的辩证批判态度。
曼弗雷多•塔夫里(Manfredo Tafuri) [⑤] (意大利建筑理论家)反对的是另一种怀旧倾向,他在《建筑与乌托邦》一书中曾对谴责大都市的非人性提出异议,他认为,在欧洲,这种情绪“只是一种怀旧病,他反对更高水平的资本主义结构,想回到人类的童年时代”。奈杰尔•科茨(Nigel Coates)也欢迎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⑥] 所说的“在大城市中的无数空间,人们可以站在这种真空的边缘上”,他反对最近的现代主义(指后现代主义)把建筑史作为风格史来研究。理论家们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提醒我们现代主义与 经济的紧密关系,如果仅把它作为风格流派来研究必将走入歧途。
3
现代主义已经被试图强制性完成现代性的理论家们宣布死亡近40年(菲利浦•约翰逊早在1959年就宣布过现代主义的“死亡”),现在,甚至后现代主义都早已退出建筑舞台,为什么还要重提现代主义呢?勒•柯布西耶曾说道:“我只有一个老师,就是‘过去’;也只有一个原则,就是‘研究过去’” 。我热衷于挖掘被尘封的历史档案,企图让历史中沉默已久的声音重新讲话。
现代主义不仅仅是单纯的美术流派,它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它还在西方的意识形态中起着很大作用。十九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现代 革命给西欧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因而艺术家和建筑师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也感受到这种变革。在将近一百年的漫长过程中,现代主义艺术家们提出一个又一个的主张和实践,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的运动。但当它获得成就之后,衰微之感便随之而至。现代主义好像一匹驰骋沙场的战马,如今垂老力竭,奄奄一息在衰草夕阳里。眸回往日,我要说的是,现代运动不象传统风格,因为它没有提供现成的结果和法式,而只是提出有条理的建议,去完成各种各样、无法预测的结果,基本上是在于程度的评价。因此,论文研究的领域部分属于历史范畴,但它所针对的目标则是现代。
马克思、尼采和他们的同代人完整的体验了现代性,当时世界上只有一小部分地方可以称作现代。一个世纪以后,现代化的进程已经抛出一张网,没有人可以逃避━甚至在世界最遥远的角落。我们可以向最早的现代主义者学到许多,不是关于他们的时代,而是关于我们自己的时代。
看起来回顾可能是前进的一种办法:记住19、20世纪现代主义可能给予我们的想象力和勇气,从而去创造21世纪现代主义。回顾过去能帮助我们找到现代主义的根源,因此它可以滋养和复兴现代主义,并勇敢的面对前面存在的艰难。对昨日现代性的评述可以立即成为当今和以后人们对现代性信念和行为的评价。
4
对于中国这个现代性迟到的国家,值得我们分析的不是当代中国的建筑创作如何借鉴西方的风格和潮流,而是这些在西方转瞬即逝的风格和潮流如何通过在中国文本里的转世获得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这种历史性并不来自抽象的观念和审美自律性,而是来自当代中国具体的经济、 、社会、文化现实。我们要追问的不是理论概念体系与现象的机械对应,也不是作为权宜之计的概念借调,而是现象和理论,或实验和理论之间的有机辩证。
我们谈论“现代主义”与“地方主义”,不是纯粹为了满足这套话语的内在欲望,而是要对当前中国社会文化做出有效的分析,对自己所处的历史空间具备反思和批判的能力。一旦我们的视线转向中国的具体现实,我们就会感到“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抽象性甚至空洞性。这导致我们在没有现代化的情况下质疑“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没有现代性的情况下质疑“现代性”(启蒙、理性化、民族-国家等)。 [⑦]
“现代主义之后”是一幅美好的图景,在那个激发想象的“后”字前面,将是一部沉重的百年史;贯穿这部历史的主题是:革命、国家、大众、现代化。风格学、符号学、隐喻、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实际问题。只有现代主义是能深入到社会内部核心并被改造为适应于中国现实的唯一方式,现代主义的中国化、地方化问题应该再次被提到理论的书本上来。
中国的问题没有谁可以开出万灵的药方,中国的未来只能由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用自己的智慧和不懈的努力换来。“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这句国际歌里的歌词本是现代性的世俗化的启蒙观念的代表性口号(西方的历史上的共产主义者从来都是启蒙主义的信徒和现代性的鼓吹者),但大多数中国人都好像注定要在“现代之后”的天空下真正领会到它的含义。从这方面提醒我们,“地区化”这个问题的出现本身就包含了双重的历史意味:它一方面表明“现代化”过程在中国还远没有完成,还将以不同的形式反复的回到我们面前;另一方面,它也暗示着,中国现代性一定程度上的展开正是“地区化”问题的客观条件;而在此条件下出场的“地区主义”必然包含了对现代性经典理论的再思考和“重读”;必然包括对现代性的客观现实的反省和批判。对中国的初步分析和把握必须在现代性和现代主义传统内部探讨“地区化”与其历史前提之间的关系。而对中国地方化价值的判断必然涉及对当代中国社会,特别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的 经济学分析。
现代性的理解
现代性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60年代以来,西方知识界对这一热门话题的探讨方兴未艾。在全球化日盛的今天,较晚进入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发展中国家,这个问题逐渐凸显出来,显得尤为迫切。分析现代性以及用现代性的思维来探讨今天的建筑界的地方化问题,可以得到更为本质的清晰认识。
5.现代性与现代化
法国诗人、现代诗歌之父波德莱尔是最早研究艺术现代性的理论家,他的名言是“你无权藐视现在”,其著作《现代生活的画家》是现代艺术史上经典的现代理论著作。最早研究现代性的社会学家有被称为社会学“四大师”之一的席美尔,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哈贝马斯,英国剑桥大学的吉登斯,以及福柯等哲学家。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是当代欧洲社会思想界中少有的大师级学者,作为“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他被称为英国首相布莱尔的“精神教父”(曾任剑桥大学教授)。近来做了大量关于现代性的考察,他把现代性定义为:“它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现代性”大略的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 它的第一个维度是“工业主义”,第二个维度是“资本主义”,把现代国家制度作为现代性的象征。吉登斯反对现代性正在消失和分裂的观点,认为“那种主张现代性正在分裂和离析的观点是陈腐的”,也反对后现代时代将会出现的推测,把西方目前所处的时期定义为“晚期现代”(late modernity)和“高度现代”(high modernity)时期。
将吉登斯的观点对应到建筑领域,会发现同样的有“现代”、“后现代”、“晚期现代”之分。美国的建筑师倾向于结束现代主义,而欧洲的理论家却基本不认同美国的后现代主义,不主张现代性的分裂。对于这一点,法国哲学家福柯的观点是值得参考的。福柯把现代性看作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历史时期,他认为与其设法区分“现代阶段”与“前”或“后现代”时期,还不如研究现代性的态度自形成以来是怎样同“反现代性”的态度相对立的。
7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不再以“现代化”(modernization)一语来作为自己的研究价值方向,而转向“现代性” (modernity)的探讨。“现代性” 与“现代化”的差别,在于后者倾向于把现代社会的成长视为自然的过程,而前者则把这一过程和关于这一过程的话语,当成一种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加以反思。
学者们发现了现代化理论的局限,“现代化”理论貌似复杂,它的本质和基本假设却很简单:1、传统与现代之间可以画出一条明确的界限;2、传统的存在会导致现代化的失败;3、现代化必须建立在传统的社会格局被打破、旧的文化意识形态消失以及新的社会格局与理念形成的基础上。这种二元对立的假设把“传统”看作是与“现代”格格不入的文化模式,坚持这种观点的学者相信只有在西方“启蒙”以后人才又可能抛弃传统并发挥“理性”的潜能。这种简单的单线社会进化论,曾被不同社会、不同阶层视为自然而然的道理。
近十年来,社会学界对于欧洲资本主义文化的研究,证明当代西方社会的组合不仅包含与传统对立的“现代”,也包含服务与国家内部秩序和主权建构以及意识形态的“历史性”(historicity )。社会史学家E•霍布斯包(Eric Hobsbawm)发现,西欧的现代化不单纯是工业化,同时还包括“传统的创造”(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和历史感的强化。美国学者E•席尔斯(Edward Shils)发现,许多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东方国家,传统在国家 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所谓“现代化”并不是单纯的“人类解放事业”,而是与全球化、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民族-国家的 、新的权力结构的形成、意识形态的渗透形式密切相关的过程。
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发现,引发了对现存文化模式理论的重新思考,不仅对传统-现代两元对立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也揭示了“传统障碍论”的意识形态背景。
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建筑领域中,传统与现代是否可以两分?它们之间是否真的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传统文化是否真的不利于现代化?现代化是否真的已在现实中打破了传统文化?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不仅需要大量的理论探讨,更需要用“现代性”的观点回顾历史、关注实践,大量的实例分析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6. 抗拒的现代性
“抗拒的现代性”也正是福柯所说的“反现代性”,它指的是,一些后发现代化的国家在从传统向现代转进的过程中,失落了现代启蒙的环节,在抵抗发达国家的强权 时把自由、民主、理性等现代性的普遍价值一起拒绝,致力于用本国深厚的传统来反抗现代性的入侵。
“抗拒的现代性”往往出现在那些具有深厚历史文化传统的、未被殖民化过的国家中,如19世纪末相对落后的德国、20世纪20年代的意大利、以及近现代的中国等。这些国家一方面致力于快速的经济和技术的现代化,一方面顽固保存旧有精神传统,在艺术上把浪漫主义的反现代性推向公共 领域,在 上为了尽快达到现代化而实施空前的社会总体控制。它们大都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现代化,但其附带的后果是前两个国家酿制了纳粹的灾难,后一个出现超英赶美大跃进的悲剧。 上的抗拒影响到艺术领域,其中建筑最明显、最敏感。
在建筑上,浪漫主义的出现就是“反抗现代性”的第一声号角,德国19世纪末的浪漫主义、二三十年代的表现主义都是作为反理性、反启蒙的角色出现的,它影响到了后来的斯堪的纳维亚的民族浪漫主义建筑、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瑞士提契诺地区的地方主义建筑实践。可以说,浪漫主义是地方主义的最早形式,“抗拒的现代性”是其最根本的原因。所以,“反抗现代性”是理解现代建筑的地方传播和地方主义的根本。
另外我们必须认识到的是,“抗拒的现代性”并不是抗拒所有的现代性,而只是抗拒那些被强加的价值观念和物质观念,它打着抗拒的旗号,实际上却吸收了现代性的主要精髓和思想动力,所以它也是现代性的一部分,是构成现代历史的一个重要环节。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地方主义建筑,就不会把它和现代主义对立起来。
7. 颠倒的现代性
“迟到的现代性”和“抗拒的现代性”是相互对应的,正因为迟到,所以才抗拒,这是地方主义建筑总是出现在边缘地区的原因。
希腊学者乔斯丹尼斯(Jusdanis)写过一本书叫《迟到的现代性》。在当前有关现代性的文献中,现代性Modernity,基本上都是单数名词,乔斯丹尼斯的贡献是把它变成复数名词Modernities。这并不是说我们在谈论现代形式是在谈论一些截然不同的东西,现代性会呈现不同的面貌,问题的关键是你在现代世界体系的什么位置上同现代性发生关系。
实际上,现代世界体系的外缘地带长期将主要精力纠缠于上层建筑,是有其不得已的苦衷的。因为在这里不仅现代形式迟到的,即不仅在时间上要比中心地区晚,而且它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同中心地区相比较是颠倒的。在欧洲和北美,资本主义是一个从内部缓慢生长起来的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进程;当非西方世界迫于帝国主义的压力争取在自己的国家发展同样资本主义时,他们实际上只能从上层建筑开始。这些地区必须首先在思想和 领域争取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但资本主义经济仍然是一个有待实现的目标,一个未来的理想。
并且,他们在追寻现代性的同时又不得不批判现代性,这就是许多国家把民族形式与现代主义结合在一起,以示对现代主义批判接受的根源所在。
这种迟到、颠倒的现代性在建筑上产生巨大影响的例子是中国,从20年代中山陵竞赛吕彦直的获奖方案,到50年代的十大建筑,再到90年代的北京西客站,大屋顶形式一直缠绕着中国建筑界,这就是现代性迟到的国家的意识形态在建筑文化领域起到的巨大控制作用,这种颠倒的现代性基本上主宰了中国现代建筑发展的整个过程。值得庆幸的是,在结束了文化与意识形态的一场文化革命后,颠倒的现代性终于又颠倒了过来,中国开始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这个时代的中国现代建筑面临的民族化、地方化问题与意识形态主宰下的民族化出现了本质上的不同,经济基础再次成为建筑赖以存在的基石,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在新形势下寻找民族化、地方化理论的问题不可避免的会再次回到当代中国面前。
8. 未完成的现代性
现代性在过去迟到了,那么现在它完成了吗?
1980年9月,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在法兰克福获得阿多诺奖时他发表了题为“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理想”的演讲,在此,他对标榜为“后结构主义”的那些法国思想家提出警告,反对利奥塔等人把“后现代性”确立为当代理论的主要参考点。哈贝马斯博大精深,他对那些轻率和不负责任的批评启蒙时期人道主义理想和理性主义的反映十分强烈,这种他称为倒退性的思考更接近早期德国左派反启蒙的 思潮。(尼采将现代性归结为权力,哈贝马斯赞同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中主观主义的批判。)
哈贝马斯坚持现代主义,但也批评理性,只不过批评的仅仅是“工具理性”, 而且工具理性的问题仅仅在与从经济━技术领域不适当的侵入到价值领域。
联系到建筑上,7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所批判的“形式服从功能”也正是针对功能理性而发的。后现代主义用“功能理性”完全取代理性进行批判,而采用的方式却是拼贴、复古的古典装饰风格,这种肤浅的机械的做法在轻浮的理论家查尔斯•詹克斯的鼓吹下风行一时,但由于缺乏根基很快便退出了历史舞台。另一位真正的建筑理论家弗兰普顿的观点一向与詹克斯的观点相左,他并没有附庸流行观点,不想象后现代主义那样妄图颠覆现代主义,而只是引用法兰克福学派本雅明等人的观点对现代主义的工具理性进行批判,提出了批判的地方主义,其本质上还是强调现代主义的延续性。从他推崇的几位建筑师可以证明这一点。
9. 现代性与中国
对于中国来说,任何超越现代性的努力必须考虑到自身立场同这个历史长时段中尚未解决的问题的关系,否则中国的后现代就会从中国当代社会思想文化的脉络中游离出去。所以,在现代化进程尚未完成的今天,现代主义的理性思想和启蒙观念不应被我们简单的抛弃,更不应代之以西方时髦的但在中国并不合时宜的思想理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性,依然是一项未竟的事业。
现代性、地方主义与建筑师
论文讨论“地方主义”并非仅出于个人偏好和审美趣味,这样的选择是有针对性的,所指向的正是当代中国如何创作出具有中国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现代建筑、如何在突破传统束缚的同时又避免全盘接受西方现代性这个困扰中国建筑师多年的问题。一方面,传统的桎梏只有依赖于现代性的力量强行解除,另一方面,简单接受现代性又令具有深厚文化传统和强烈民族自尊的人民蒙受尴尬和伤害,这正是中国建筑创作面临的两难之境,也正是中国建筑创作长期徘徊的原因所在。也正因为如此,地方知识分子的反思便成为人类“现代性”问题的重要部分。真正深刻的反思固然依赖于每一个对话者自身的思考,但达到清晰而深刻的反思,却必须依赖于所有对话者投入到特定的立场中所产生的思考。另外:
10
建筑评论没有义务去从理论上倡导某些未来的风格,没有义务去倡导某种革命性的建筑,我们不主张某种中国式的建筑风格,也不主张某种不变的和确定的地方风格,在这样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年代,固定答案是没有的。我们能说的不是“应该怎么办”,而是“去想应该怎么办”。论文没有试图去建立一种如同古典主义那样通用的法式,这不是现代主义的方法,也不是地方主义的精神。我们象现代主义者那样,只欲提问和建议,一个问题在分解成若干小问题后,答案便已包含在其中。
11
首先我们要问,“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这种东西真的存在吗? 如果它存在的话,那么它很可能“既不是民族的,也不是世界的”,只会是一些折衷主义的杂烩拼贴。 我们不如倡导一种“陌生化”和“疏离化”的原则,把艺术创作建立在个人和自由意志的基础上,这种个人方式本身就包含了“民族性”“地方性”,因为任何人没有办法生活在真空中,任何人不可能不与他生存的土地接触。
12
在浪漫主义的“幻像”与理性主义的“镜像”中,我们应该选择什么呢?
“地方主义”从它产生时就伴随着辩证思想和批判精神,同时保持了高度的文化自觉,它在批评的同时没有把自己置身于一种普遍的文化范式加以传播。可以说,脱离了辩证法根本无法理解地方主义思想,也无法解释它和现代主义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也正是关于“地方主义”的文章都显得比较晦涩难懂的主要原因。在缺乏适当理论背景的情况下,不可能理解它的真正价值和它所具有的批判性和抵抗性。然而,对现实的批判代替不了每一个人在现实中的选择,我们将把这些概念引入到地区建筑学中:启蒙、理性、现代性、现代主义、科学主义、平等主义、自由意志。
13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曾经造就了西方启蒙和启蒙知识分子,而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把中国带入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在“全球资本主义”这个现实命题下,每个知识分子的选择是什么?是选择一往无前的进入未知的命运呢?还是选择回到自我保护的古老传统中去?作为知识分子的建筑师,或作为建筑师的知识分子的反思便成为中国“现代性”问题的重要部分,这种真正清晰而深刻的反思依赖于所有对话者投入到特定的立场中所产生的思考。
“走向世界”是中国人长久以来的现代性梦想,然而近百年来唱着《国际歌》却不能走向世界,呼喊着“现代化”却不能建立自己的现代性。中国现代思想在近百年的现代历程里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现代性,我们还得再次呼唤—呼唤理性,呼唤启蒙,呼唤现代性事业,呼唤尊重那些从事这一艰难事业的知识分子。
结语:“启蒙地方主义”
何谓启蒙?启蒙是一种对待传统的永恒态度。在中国“现代”旅途上,只有启蒙能让我们看清自己,看清自己所处的地方、所处的阶段,也只有启蒙能让中国地方建筑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启蒙地方主义”,一种理性地方主义,它消解了整体与局部的对立,现代与传统的对立,全球与地方的对立,宏观叙事与微观因素的对立,作为人类整体文化与基本单位之间的对立,从而渐渐形成自己的建筑和文化范式。如果我们决心不利用人类知识的整体,而仅仅依靠我们的地方经验和传统,那么我们将回到原始时代或“前原始生活”方式中。最后,我想引用中国学者汪丁丁的一句话来结束我的思考:“启蒙死了,但作为个人自由与普遍主义原则的启蒙精神还活着。”
(全文完)
(2000/6初搞,2002/1二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波德莱尔:法国诗人,被誉为“现代诗歌之父”。
[②] 哈贝马斯: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被称为“20世纪后半期最杰出的社会问题理论家”。
[③] 标题引自《 宣言》中的一句话。
[④] 肯尼斯•弗兰普顿:建筑理论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现代建筑与批判的现在》、《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构造文化研究》。
[⑤] 曼弗雷多•塔夫里:意大利建筑理论家,其主要著作有《现代建筑》、《建筑历史理论》、《建筑与乌托邦》。其中《建筑与乌托邦》被詹姆逊认为是与罗兰•巴特的《写作的零度》和阿多诺的《现代音乐哲学》齐名的社会学著作。
[⑥] 沃尔特•本雅明(Benjamin Walter,1892-1940)二十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德国文学评论家。被认为是马克思人道主义的阐释者,他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分析劳动者的地位和对异化的批评以及资本主义环境下的人的意识“具体化”等方面对美学的重要贡献。本雅明的评论文集《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1936)试图描述艺术在现代世界变化的体验。
[⑦] 著名的历史学家周谷城先生为近代中国做了一个总结,认为欧洲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告终,用280年穿越了近代,而中国近代史为时不过80年,所以中国没有能完成资本主义生产,也没有培育出资产阶级及其文化。(《中国通史•下册》) |
|
 如果你在论坛求助问题,并且已经从坛友或者管理的回复中解决了问题,请把帖子标题加上【已解决】;
如果你在论坛求助问题,并且已经从坛友或者管理的回复中解决了问题,请把帖子标题加上【已解决】; 如何回报帮助你解决问题的坛友,一个好办法就是给对方加【D豆】,加分不会扣除自己的积分,做一个热心并受欢迎的人!
如何回报帮助你解决问题的坛友,一个好办法就是给对方加【D豆】,加分不会扣除自己的积分,做一个热心并受欢迎的人!
 |申请友链|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辽公网安备|晓东CAD家园
( 辽ICP备15016793号 )
|申请友链|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辽公网安备|晓东CAD家园
( 辽ICP备15016793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