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ID
- 79631
- 积分
- 0
- 精华
- 贡献
-
- 威望
-
- 活跃度
-
- D豆
-
- 在线时间
- 小时
- 注册时间
- 2003-9-15
- 最后登录
- 1970-1-1
|
马上注册,结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让你轻松玩转社区。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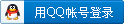

×
一、
凌晨。零点四十五分。
窗外雨急风骤,阿雾不知去何方买醉未归。阿雾是我的大学时的朋友,她近来失恋,那天半夜背着行李来投靠我——那个有妇之夫,对她的感情予取予求,需索无度,最后竟然视之如敝屐,不闻不问,扬长而去。
而我因为需要静养,托朋友在青澳湾找了间房子一个人住下,闲时给地方小报写写稿。她请了假来找我,一为散心,二为避难——她说这是一场浩劫,让她遍体鳞伤,心也支离破碎。
我将电脑上刚打的稿子保存,伸了个懒腰,打算洗刷后睡觉。
这时门铃响了,我趿着拖鞋去开门。门口,醉醺醺的阿雾被一个男人掺扶着。
“唉呀阿雾,你又喝高了。”我摇摇头,那个男人帮我把阿雾扶进客厅的沙发上,我为阿雾脱了鞋子和外套。拿了脸盆想去盛点水来给她擦脸去去酒气,突然看到那个男人还在客厅的角落站着。他背对着灯光,我看不清他的脸。我没想太多,阿雾的私生活,我不关心。
我对他感激而报歉地笑了一下:“我来照顾她好了。谢谢你送阿雾回来。”我想他应该就此离开。所以转身走向浴室。
这时,我听到一个声音犹豫地、缓慢而又准确地念出我的名字:“江凡雁……”
这个声音,曾经在我心里梦里回响过千百回,而此刻真真切切地听到,竟觉得如此陈旧而遥远,像是前世某个片断不小心保存在了今生的记忆里。
我愣住,泪水一下子涌出眼底。我没敢回头,因为我发誓过,不会再在这个声音的主人面前流泪。
“我去盛水给阿雾擦脸。”我低低地说,快步走向浴室,脚底下感觉像在腾云驾雾。
热水慢慢注进脸盆,水蒸气的氤氲模糊了浴室里的镜子,也慢慢舔湿了我的脸。我将冷冰的双手浸入水中,脑中一片空白。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等待着与信宁的重逢。我知道,我们一定会再次相遇。而那个相逢的场面,无数次在我梦中出现,应该是这样的:还是在那个美丽宁静的海滨小城,还是在那条寂寂的海滨长廊,深秋的黄昏的夕阳中,我穿着象牙白的毛衣,红黑格子的苏格兰裙,披着红色的羊毛围巾,仰着苍白素雅的脸庞,在归船的汽笛声中看海。这时,他走过来,在我身边停下,坚定而忧伤地轻轻唤一声:“阿雁,你好吗……”
而不应该是现在这样:在这个凄风冷雨的小岛,简陋的小公寓里,我,长发披散,面带菜色,两眼发红,嘴唇发青,穿着白色的旧棉布睡裙,趿着拖鞋,状若孤魂野鬼。而他,扶着喝醉的我的女朋友,闯进我原来寂寞安宁的一屋灯火中。
生命中为什么要有这么多令人防不胜防的因缘错合,让我们时不时地陷入这种不知所措的尴尬中?
我望着镜子哀哀地笑了。重新盛了热水,飘回客厅,坐在醉得一塌糊涂的阿雾旁边,默默地给她擦脸,擦手。
信宁还是站在角落里。
空气中一种凝固的沉默。除了阿雾喃喃的醉语:“阿凯……我不行了……带我回去……救救我……”
“阿雾,到床上睡去吧。”我低低地说,扶起她沉沉的身体。信宁急忙走过来,帮我扶起阿雾,这时,他好像找到了什么可以说话的借口一样,急急地说:“我不认识她。我是来这里考察一个项目……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在这里教书,所以跟他一起在酒吧聚聚。你的朋友跟我同学认识,他们都喝醉了,在里面摔酒瓶子……只有她一个女孩子,我先送她回来。我不知道你在这里……”
我用力打掉他扶住阿雾的手:“多、谢,我自己来就行了。不好意思,扰断了你一个艳遇的计划!”
他气得哑口无言,半晌才低吼:“我是那么不堪的人吗?!你,你怎么还是这个样子!”
“对不起,我就是这个样子。”我冷笑一声,厉声道:“你不必强调你不知道我在这里,我有自知之明,不会自做多情地以为你是千里迢迢蓄谋已久地来找我!反正只是冤家路窄无意间狭路相逢,那么你现在就可以走了,你早就可以走了!”
我咬牙切齿地把阿雾连拖带扯地弄到床上,心中另一个声音在悲哀地说:“他已经跟你没关系了,为什么你还这么在意他的一字一句呢?你们一在一起,还是会互相伤害……”
我坐在床沿,听见大门打开的声音,然后是重重的一响——他,走了。
我赤着脚跑到客厅,赫然见他还立在门边。
一切似乎是时光倒流的一幕。那时候,我们俩一吵架,结果总是我跑到床上哭,以为他摔门而去跑出来时,却总会发现他还站在门边,这时他会笑着说:“看,你还是舍不得我的吧。”……
然而现在,他只是一脸的茫然。
一种似曾相识的忧伤突然袭击而来。我喃喃地说:“对不起。”
他默默地走回来,站在我面前。他依旧颀长儒雅,而我变得单薄憔悴。
“你瘦了很多。”他的声音嘶哑。
我故做潇洒地耸耸肩:“不止是瘦了很多,而且老了,丑了。女人哪……一不小心,就变成了明日黄花,蝶也愁了。”走回沙发上,盘起脚,缩着身子。
他也走过来,在另一张沙发上坐下。
“这些年,你……过得好吗?”他问。
“穷困潦倒,卖字为生……无所谓好,也无所谓不好。日子总是要过的……”我自嘲地说。
“你没在那个杂志社工作了?那份杂志是我唯一可以得到你的消息的来源,看到上面还有你的名字,我就知道你还好好地呆着。后来,看到那份杂志以前你负责的栏目换了编辑……”
“我没办法再在那个城市呆下去了。”我伤感地说,“所以,做回自由撰稿人,四处漂泊,”
“你为什么会跑到这里?
“这阵子有点神经衰弱,跑来这里静养。这里空气好,民风也好,没有压力。”我认真地回答他。然后又急切地问:“你呢?”
“还可以,每天都很忙。”
“她呢?”我低下头。
“她很好……我们……十二月结婚。”
我霍地站起来,转过身走到窗边:“好冷。关一下窗子……雨都泼进来了……昨天天气还好好的,今儿个一雨成秋了。”我站在窗前,把脸置于秋风秋雨的清冽寒意中,任泪水肆意奔流。
他也走过来,站在我身后:“你哭了。”
“没有,砂子呢……”我哽咽着说。
“你总是这样。”他无奈说,“每次一哭,都说是有砂子。”
“你走吧。”我没有回头看他。
良久,开门声、关门声——我知道,这回,他是真的走了。
窗外雨下得更急了。我注视着信宁的背影在雨中慢慢流逝。我慢慢关上窗子,窗户的玻璃不知何时裂了几条缝。而班驳的过往,一如玻璃,那样的易碎……
二、
与信宁分手的那天,也是下着大雨。
“江凡雁,我再问一次,你到底跟不跟我走?”他脸涨得通红。
“不!我为什么要去那个拥挤的、拜金的、乱七八糟的城市!而且,你既然已经不爱我了,我还要跟你去做什么?”我瞪着眼,叉着腰。
令我失望的是,我的最后一句话他没有否认。他只是大吼:“你莫明其妙!你不要老是顾左右而言他!”
“你怕我言‘她’是吧?你怕什么?你喜欢她就叫她跟你去好了。她肯定手足并用爬都跟你爬过去!”
“你,除了越来越尖酸刻薄,你还有什么长进的?”他指着我的鼻子。
我自尊心严重受损:“你,除了越来越花痴,还有什么长进的?见到个稍微齐整的女人,就跑过去管人家叫老婆!”
他愣住了。我也讪然低头不语。
我所说的“她”是他的一个女同事,从一见到她,我就觉得她对信宁态度暧昧,所以对她一直深有敌意——是的,我爱信宁爱得发疯,而他是那样优秀,那样惹女孩子注目。我的疑心与日俱增,我不确定他爱不爱我,或者,爱得有多深——因为,他从来没有许诺过我未来,比如婚姻,比如家庭。
有一次无意间看到他手机的短信息,上面说:“信宁,还不来,你老婆在这里等你呢。”我火冒三丈,回信息问:“我老婆?是谁?”那边再回一个过来:“XXX啊,你上次当众叫过她‘老婆’的,做过的事不能赖啊!哈哈!”……
他向我解释说,那是他们同事间一次午休时玩的游戏。他们打牌,谁输了谁就得跑到办公室中间,对正在加班打文件的她说:“老婆,我爱你。”结果,他输了。
我不管,我妒火中烧,我寻死觅活,开始了与信宁的第N次战争。这次战争为期两个月后方才结束。这时,信宁提出,想跳槽到省城去,他学计算机的,那里的IT业能给他更大的发展空间。
我不同意。我觉得我们现在所在的海滨城市,美丽可爱,舒服温暖,而且我最怕的是,到了那个繁华的都市后,我会对自己更没有信心,对信宁的把握会更小。我怕输了他,就会输了全部。
“阿雁,你不觉得,我们相处的这几年里,吵架的时间太多了吗?”他开口了,眼眉间一片疲惫,“我们总忙着互相猜疑,中伤。我真的累了。我对我们之间已经不再有任何信心与希望了。我们分手吧。这样彼此也好过一点。”
这是他首次提出分手。我一阵晕眩。
“我知道,是我不够好。你喜欢安定,喜欢无微不至的照顾,喜欢舒舒服服地过日子,这些都无可厚非。可是,我现在真的还做不到……我的压力很大,社会的、家里的……我现在无法让你过上你希望过的日子,所以,也许我真的不适合你。”他黯然地说。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气愤地说,“这个借口,怎么那么多个男人喜欢用。你太俗气了。信宁。既然你认为我们之间已经没有感情了,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信宁的脸上一片灰白。我浑身发抖,欲哭无泪。
大雨如注。
他打开门走了,我站在窗前,看他在雨中蹒跚地走到路边,等车。雨天,计程车的生意很好,他在雨中等了五分钟了,还等不到车。
“信宁,信宁……”我的心开始作痛。我找出雨伞,飞奔下楼。我感觉这一次是我跟信宁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不同于以往的争吵,我们把对方已经伤到了极点。
信宁全身已经湿透,全身颤抖,与他相识这么久,我从没见他这么冷过,这么脆弱过。我紧紧依着他的身子,右手撑着伞,他的左手包在我右手之上,用力地握着。我的长发在风雨中纠结,雨伞形同虚设,全身也慢慢湿透。我闭着眼,心中祈祷:“信宁,如果现在你说你爱我,我就跟你走,不管去哪里,我不要名份,不要工作,不要舒服……信宁,我还是爱你的,你能听到吗?我还想让你带我飞翔,你能懂得吗?信宁,说你爱我,快说……”
这时,一辆空车来了,缓缓地停在我们身边。信宁看了我一眼,用力地抱了我一下,打开车门进去,车门砰然关上。
我与信宁这三年的感情仿佛就只隔着这道车门,门外是缘起,门里是缘灭。
车,开走了。一切都来不及了。那一刻,我觉得我的青春骤然褪色,呼吸成为多余,生命不再延续。
许久,我往回走。不知道走了多久,回到家,才发现手中雨伞已不知所踪。
我站在窗前对着雨幕,喃喃地说:“信宁,你永远不知道我有多爱你。”
我没有再找过信宁,因为,我知道,以我与信宁的性格,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为对方改变。就算我们再在一起,也无法终成眷属,白头偕老;而且因为,我听说,“她”真的也去了省城。
一切都可以预料。我心若死水。
可是我仍然相信上天会再安排我们重逢。是的信宁,事到如今我依然爱你,我孤孤单单留在回忆里,好想陪你再淋一场雨,让世界再次为我们停止呼吸……
三、
阿雾一直睡到翌日中午才醒过来。她揉着发红的双眼:“对不起,阿雁,昨晚我又喝高了。”
我无言,继续打稿子。
“阿雁……”阿雾蜷着身子坐在地上,“我从来没想到我会这么狼狈……我不想活了。真没意思。我真没用,为了个男人弄成这样子。”
“一切都说不清楚。爱的太狂烈,注定伤的是自己。就当是你前生欠他的吧。”我叹息着说,“都是五百年前的风流债,要今天来付本还息啊。”
“阿雁……你当时失恋,是怎么过的?”她茫然地问。
“心已经裂成碎片,想捡起来都嫌扎手。”我苦笑着说。“所以,我已经不想谈这个问题了。反正,我绝对不会去学抽烟,也不会去酗酒,本来心已经老了,再让容颜憔悴,岂不是输到极点。”
阿雾走到我的桌边,看着我桌上插的那株绿萝。“好盎然的绿色。”
“那天在一堵围墙外,看到它被一些小孩子摘下,又丢在地上,我随手捡回来,插在瓶中,竟然也就活下去了。”
“我们呢,我们的爱是不是也可以像这种植物一样重新生长,不再有过去的伤痛?”阿雾的眼泪滴了下来。
“阿雾,不是所有相爱的最后都可以在一起。”我无奈地说,“更何况,你已经回不到过去了。”
“阿雁,你就不能安慰鼓励我一下吗?”阿雾泪汪汪地、怨恨地看着我。
本来是可以的,我在心里说,可是,谁叫你给我惹祸来,现在又有谁来安慰鼓励我呢?
我看看窗外,雨已经停了,一片大好秋色。南国的秋天,风清云淡。可是对于失恋的人来说,无论太阳多好,都是惨淡的。
晚上,阿雾留在房间里看书。
这时门铃又响起,我心脏瞬间收缩。
阿雾去开门,过了一会,她走过来,拿了一封信给我:“是赵明,前几天我在酒吧里认识的。他说他的朋友,昨晚我见过的,叫做信宁,托他拿这封信来给你。”
我的心脏开始跳得很厉害,久违了的感觉。
阿雁:
不知道老天安排我们的这次重逢,是对我的恩赐,还是惩罚。我原来以为,当一切已经过去,我就会慢慢忘了你,从此心中的重担就会卸落,就会去投奔自己的幸福。可是昨天晚上,见到你之后,我发现自己完全不能心静如水,回来后,依旧心乱如麻。是的,阿雁,我依然爱你。
我一直地在想离开你的那一天的情景。我们在雨中依偎,那一刻,我觉得世界上就只有你能与我相依为命,我在心里对自己说:阿雁,如果你现在说愿意跟我走,以后,我就要用了全部的努力来给你幸福,来实现你喜欢过的那种生活。可是,你始终沉默着,或许,是我太令你失望了吧。
当时,你总是不信任我的感情,都怪我,以前我太年轻,太轻浮,太怯懦,太自卑,所以不敢对你承诺未来。那天进入计程车,关上门的那时,我说:‘阿雁,我爱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
我之所以要写这封信告诉你这些,是因为,我知道我必须要向你做最终最彻底的告别,我再也无法承受与你的再一次相见与别离。我已经把未来许诺给她了,她是个好女子,这些年来跟着我漂泊打拼,受了很多苦。所以,我会为了她而成为一个好丈夫。
阿雁,如果老天不想让我们终成眷属,我希望,从此我们不要再见。
信宁
原来以为,我与信宁的未来可以是一串长长的省略号,现在我才知道,这串省略号,已经划成一个圆满的句号了。而这个圆满对我来说,却不是幸福。这么多年以来,我用爱织了一张网,网来网去,网住了自己,却赶走了爱情。
我合上信纸,对阿雾说:“阿雾,让我和自己静静地相处一晚,好吗?”
阿雾点点头,默然离开。
屋里一片寂静,我听得见自己的呼吸,清楚地知道自己活着的消息。我站在窗前,窗外月光如水,美好安静得就像一个梦开始的地方。我缓缓推开窗子,这一刹那,所有的忧伤不请自来。
四、
阿雾死了。就在我叫她让我独处的那个晚上,半夜,她在旅馆里,用刀片切断了自己的静脉。
我赶到的时候,她已经奄奄一息。她脸色青白,双目圆睁,攫紧了我的手:“阿雁,我知道这样做很傻。但是,我每天都发疯似地想他,我依然爱他……我知道我已经没办法让他回到我身边了。我恨他!我要报复他。我没有其他办法,我只能用自己的生命,来让他悔恨负疚一生!”
最后,她说:“把我的骨灰,葬在家乡山上的天池边……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因为我的命太贱了。对我父母说,我对不起他们,来生,来生——”她的头歪向一边,声音越来越小。
我把她的头扶正,在她耳边小声说:“我知道了……阿雾,睡吧。”用手轻轻在她脸上抚过,让她的眼睛阖上。她安详得如同睡去。
我怔怔地望着她,我是杀死阿雾的间接凶手。想到这里,我心中的某个角落塌陷,阿雾的名字如同空谷回音在里面轰鸣,而我却说不出一句话,眼中也流不出一滴泪水。
原来,爱也可以变为一种伤害,而且是最致命的。
一星期后,我背着阿雾的骨灰,来到她的家乡。阿雾生前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减肥,而现在,她轻得只有几十克。她是不是如愿以偿呢?生于尘,归于尘,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
那座山,主峰海拔1391米。我从早上就开始爬山。一路磕磕碰碰,攀岩涉水,傍晚到达顶峰时,风尘满面,灰土满衣。
天池云烟浩缈,水面澄然如镜。这个地方,阿雾告诉过我,传说是西王母沐浴之地,我下到岸边,洗脸濯足,涤荡尘埃。看着天蓝如洗,夕照满湖,草绿如茵,落霞似锦。我似乎突然间心灵性明起来。我明白了阿雾为何选择这个地方安家。
在池边一棵松树下,我掘了个深深的坑,把阿雾安葬在里面。阿雾,这里离天堂很近,你在天堂里,天堂在我心中,所以,你永远在我心里。
做完这些,我在一块大石上,极目远眺,坐看云起。耳边恍惚响起信宁的声音:“阿雁,我依然爱你……”信宁,那时,我来不及告诉你,我爱你。现在,我却已经再没有机会告诉你——我爱你。
我站起来,圈起手掌,向着飘缈的远山大声喊:信宁,我——爱——你——
远山回音:我——爱——你……爱——你……你……
不久,一轮弯月淡淡地升起。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唯有山与月,相看两不厌。我想,这山与月应该是相爱着的吧。这山,这月,从古到今,长相厮守,相看不厌。而相看两不厌,是否就是相爱的最高境界?不像我们,相爱着,却总是要互相伤害。
阿雾,你说你依然爱他。信宁,你说,你依然爱我,我也说,我依然爱你。可是,无法相守,无缘相惜,爱又如何?爱又如何?! |
|
 如果你在论坛求助问题,并且已经从坛友或者管理的回复中解决了问题,请把帖子标题加上【已解决】;
如果你在论坛求助问题,并且已经从坛友或者管理的回复中解决了问题,请把帖子标题加上【已解决】; 如何回报帮助你解决问题的坛友,一个好办法就是给对方加【D豆】,加分不会扣除自己的积分,做一个热心并受欢迎的人!
如何回报帮助你解决问题的坛友,一个好办法就是给对方加【D豆】,加分不会扣除自己的积分,做一个热心并受欢迎的人!
 如果你在论坛求助问题,并且已经从坛友或者管理的回复中解决了问题,请把帖子标题加上【已解决】;
如果你在论坛求助问题,并且已经从坛友或者管理的回复中解决了问题,请把帖子标题加上【已解决】; 如何回报帮助你解决问题的坛友,一个好办法就是给对方加【D豆】,加分不会扣除自己的积分,做一个热心并受欢迎的人!
如何回报帮助你解决问题的坛友,一个好办法就是给对方加【D豆】,加分不会扣除自己的积分,做一个热心并受欢迎的人!
 如果你在论坛求助问题,并且已经从坛友或者管理的回复中解决了问题,请把帖子标题加上【已解决】;
如果你在论坛求助问题,并且已经从坛友或者管理的回复中解决了问题,请把帖子标题加上【已解决】; 如何回报帮助你解决问题的坛友,一个好办法就是给对方加【D豆】,加分不会扣除自己的积分,做一个热心并受欢迎的人!
如何回报帮助你解决问题的坛友,一个好办法就是给对方加【D豆】,加分不会扣除自己的积分,做一个热心并受欢迎的人!
 如果你在论坛求助问题,并且已经从坛友或者管理的回复中解决了问题,请把帖子标题加上【已解决】;
如果你在论坛求助问题,并且已经从坛友或者管理的回复中解决了问题,请把帖子标题加上【已解决】; 如何回报帮助你解决问题的坛友,一个好办法就是给对方加【D豆】,加分不会扣除自己的积分,做一个热心并受欢迎的人!
如何回报帮助你解决问题的坛友,一个好办法就是给对方加【D豆】,加分不会扣除自己的积分,做一个热心并受欢迎的人!
 如果你在论坛求助问题,并且已经从坛友或者管理的回复中解决了问题,请把帖子标题加上【已解决】;
如果你在论坛求助问题,并且已经从坛友或者管理的回复中解决了问题,请把帖子标题加上【已解决】; 如何回报帮助你解决问题的坛友,一个好办法就是给对方加【D豆】,加分不会扣除自己的积分,做一个热心并受欢迎的人!
如何回报帮助你解决问题的坛友,一个好办法就是给对方加【D豆】,加分不会扣除自己的积分,做一个热心并受欢迎的人!
 如果你在论坛求助问题,并且已经从坛友或者管理的回复中解决了问题,请把帖子标题加上【已解决】;
如果你在论坛求助问题,并且已经从坛友或者管理的回复中解决了问题,请把帖子标题加上【已解决】; 如何回报帮助你解决问题的坛友,一个好办法就是给对方加【D豆】,加分不会扣除自己的积分,做一个热心并受欢迎的人!
如何回报帮助你解决问题的坛友,一个好办法就是给对方加【D豆】,加分不会扣除自己的积分,做一个热心并受欢迎的人!
 |申请友链|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辽公网安备|晓东CAD家园
( 辽ICP备15016793号 )
|申请友链|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辽公网安备|晓东CAD家园
( 辽ICP备15016793号 )